请登录查看大图。42+万用户选择下载看福清App享受全功能!
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,没有账号?立即注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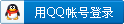 |
|
x
头天晚上到福清,第二天上午就去玉融山走栈道,走到一个视野开阔处,顺着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放眼望去,绿树掩映,山峦叠翠,如水般明净的阳光笼罩着城市,如梦似幻,让人心生无限遐想。 这是我第一次到福清。我不是去游山玩水的,不是去走栈道的,也不是去欣赏城市建设的。走南闯北数十年,名山大川哪里都有,古刹新阁随处可见。但凡到一个城市,我都有一个期待,期待新的发现,新的见识,新的激动。 1 多少年来,有几个名字一直萦绕心头,读书的时候,写作的时候,这些名字总是在我的耳畔飞翔。特别是最近几年,我逐渐集中于英雄书写,每当提起笔,每当构思塑造一个人物,这些从未谋面的人物就会出现在眼前。 出现最多的那个人,名字叫林则徐,这不仅因为他是个政治家、军事家,更因为他是个改革家。在闭关锁国的清朝,林则徐编译了《四洲志》,被誉为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,我揣摩他的雄心是编一部《地球传》,他要搞清楚我们中国在世界的位置,他要搞清楚,我们中国到底是不是可以立于世界先进之林。 中国的知识分子,强调修齐治平,达则兼济天下。但是更多的人,心里有英雄追求,行为上做不到,只好“穷则独善其身”了。林则徐做到了,从力排众议禁烟,到忍辱负重戍边,到死都在考虑国家民族利益。也是这个人,发现了人才左宗棠,倾心提携并授以治疆大计,所以才有左氏在新疆长治久安的大业。 福清是林则徐的故乡。我感兴趣的是,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,为什么独独在这块土地上生长了“睁开眼睛看世界”的第一人?连续几天,我们走了很多地方,有一个名叫东关寨的地方特别令人难忘,那是一座山区家族聚居式古寨,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军事防御堡垒。据说,鼎盛时期这座寨子可以容纳两千多人的宴席。想象两千多人集聚在一个寨子里,该是怎样的盛况,不仅显示着物资的丰饶,更体现了一种生活态度――群山腹地,白云深处,阳光之下,绿荫丛中,民风淳朴,其乐融融,俨然一个诗意栖居的世外桃源。可是,这样的光景,有多少人能够享受得到呢?又能够持续多久呢? 古寨的西南方,有一株蘑菇云一般硕大的榕树,据说高龄已在五百年以上,生命之根深植于土地,蔓延方圆数里。这棵老树见证了古寨的繁荣与衰落,饱经风霜的树干写满了近代历史的雄阔与苍凉。林则徐生长在海口镇的岑兜村,距离此地不远,那些穿透地表四处探索的根须,于无声处传递着历史的脉动,倾诉着一方水土的传说,滋养着一个少年、一个青年的骨骼和神经。 林则徐的成长当然与这片土地有关,更与弥漫在这片土地上面的历史气息有关。
2 在海口镇瑞岩山,拾级而上,一座巨大的石雕出现在眼前,弥勒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。心中顿时一热,不管世道怎样艰难,无论生活怎样贫苦,只要有希望,就会有快乐,只要有快乐,就会有希望。弥勒石雕裸露的皮肤上已经锈迹斑斑,但这丝毫不影响这尊佛爷笑看人间的气度,它的眼睛里永远洋溢着宽容、欣慰、欢乐、慈祥的笑容。说不清是神创造了人,还是人创造了神,但是,人永远需要神,永远需要在心里注入一股希望的、快乐的精气神。 转过身去,我看见了另一道风景在弥勒佛左前方,有一块桌面大小的黑色石碑――戚继光抗倭遗迹。我的腰杆本能地挺直了,大步走向石碑的正面,众目睽睽之下,庄重地立正,举起右臂,敬了一个军礼――尽管那天我没有穿军装,但是我以军人的肢体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,我的右手食指紧紧贴在额头上,我听到了从我手指上传递出来的内心的庄重的敬仰。是的,我敬仰这个先辈,自从我四十年前从军,自从我三十年前成为一名军旅作家,他就一直是飘扬在我头顶的一面旗帜。就是这个人,把一支散兵游勇整饬成一支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;就是这个人,带领装备极其落后、给养十分困难的部队,从东北沿海打到东南沿海;就是这个人,开风气之先,写下了《练兵实纪》《纪效新书》等颇具现代军事思想的兵书。二十年前我创作长篇小说《仰角》,就是从戚继光的《练兵实纪》里受到启发,从而明白了“训练”二字的初心――“训”,为思想政治工作;“练”,为体能、技能、智能提高。训为练之魂,练为训之手。可以说,戚继光是古代抵御外侮、把仗打得最扬眉吐气的将军,也是最早觉悟到对部队进行精神培育重要性的将军,还是一个把思想训导和军事练习结合起来的军事理论家。 在福清,同时得到戚继光和林则徐的信息,让我浮想联翩。这两个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,戚继光的舞台,正是林则徐的故乡。戚继光生于1528年,比林则徐年长257岁,他们促膝长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,但是,我执拗地认为,林则徐对戚继光并不陌生,那远去的战马嘶鸣,那消失的刀光剑影,并没有真正离开,从来没有离开过,他们化成了阳光和雨水,进入到福清的山脉沟壑,潜伏在东关寨的砖墙的缝隙里,渗透到古榕树的枝叶神经里,等待着,等待着又一个铁血男儿问世,等待他来聆听过去的故事,等待他来呼吸几百年前旌旗飞扬的猎猎雄风。 从“繁霜尽是心头血,洒向千峰秋叶丹”到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,从戚继光到林则徐,从福清到虎门,从东南到西北,英雄前行的漫漫长夜,总有璀璨的星星相伴。
3 在一个小镇上,目睹了一对父女展示祖传的手艺,烘制一种名叫“光饼”的食物。烘制过程惊心动魄,一炉熊熊燃烧的柴火将炉子的内壁烧至高温,六十多岁的父亲先是火中取栗般将面饼贴在内壁,又虎口拔牙般将饼从炉膛取出。一筐光饼搬到车上,主人叮嘱我们,趁热吃,越热越香。果然,一口咬下去,香味扑鼻而来。 当地人说,光饼的名气很大,走得再远,只要能吃上光饼,就算回到家乡。很多海外游子,拒绝接受洋人的汉堡包,经常快递家乡的光饼。 我注意到光饼的材料和制作工艺,跟我老家的烧饼大同小异,要说味道,也出奇不到哪里去。区别在于,光饼不是一般的食品,而是“有文化”的食品,之所以名气大,不是从营养学的角度衡量,也不是从味觉审美的角度衡量,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衡量。 相传,在戚继光抗倭时代,为了解决给养问题,戚继光指示麾下的伙夫,研制一种便于携带、能量充足的食品。伙夫借鉴山东煎饼做法,不断改良,逐步完善,于是就成了流传至今、名扬海内外的“光饼”――戚继光饼。我吃光饼,首先想到的是,这应该是压缩饼干的前身。在那个年代,在那样的环境里,能够发明出压缩饼干,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戚继光具有改革的前瞻意识,视野开阔,博采众长,这是我在众多的值得敬仰的先辈英雄中,首推戚继光的原因。 齿留光饼余香,我们驱车到了海边。 站在福清的海岸线上,放眼望去,就是台湾海峡。我不知道这片海域的海沟有多深,但是我知道,这片海域沉淀了太多的记忆,最深刻的,还是那些抵御外侮、民族自强的篇章。此刻,此岸,一个强劲的声音像涨潮一样一浪高过一浪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统一……东关寨下的那棵大榕树啊,它的密密麻麻的根须,正在触摸海峡的温度。那高耸入云的树冠,是戚继光的眼睛,是林则徐的眼睛,是炎黄子孙的眼睛,正在眺望,正在寻找。越过百年沧桑和千里波涛,在海鸥飞翔的海面上,我们的视线正在对接。
文章发表于《解放军报》2019年11月11日长征副刊
作者简介

徐贵祥,安徽省六安人,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。曾任解放军出版社总编室主任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仰角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高地》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《明天战争》《特务连》《马上天下》《四面八方》《对阵》等。获第七、九、十一届全军文艺奖 ,第四、九、十一届“五个一工程奖”以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。
|